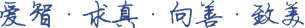徐弢:士林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關係的再思考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2-01
内容摘要:
在對中世紀士林哲學史的研究中,士林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間有無真正的內在聯繫是一個聚訟紛紜的焦點,而當代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又主要源自對信仰在哲學中有無積極作用的不同看法。部分學者把信仰一概視為對理性的外在干擾或束縛,並因而否認士林哲學是一種同基督宗教信仰有內在聯繫的哲學;但在那些堅持把士林哲學定義為基督宗教哲學的學者看來,信仰作為理性的必要補充或基礎,則對哲學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通過梳理爭論雙方的代表性觀點並反思其中存在的絕對主義傾向,我們試圖對士林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合理性”問題做出更具體的分析。
关健字:
士林哲學 基督宗教哲學 信仰 理性
在剛走出“黑暗時代”的10世紀,有“第一位士林哲學家”之稱的聖安瑟爾謨(St. Anselm)便按照聖奧斯定(St. Augustine)等教父開創的理性辯護主義傳統,確立了“信仰尋求理解”和“哲學是神學之婢女”的理論原則。此後的各派士林哲學家在按照上述原則改造希臘羅馬哲學的過程中,使信仰與理性在他們的學說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調和。至13世紀,以士林哲學為基本形態的基督宗教哲學逐漸進入鼎盛期。聖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通過將亞裏士多德等人的哲學與基督宗教神學融為一爐,建立了迄今仍有深遠影響的基督宗教哲學體系。同時代的聖文都辣(St. Bonaventure)亦曾通過對理性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分析,來說明哲學的“內在之光”與神學的“信仰之光”源自同一上帝。
因中世紀士林哲學家往往以基督宗教信仰作為論證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又在涉及的問題和探討問題的方法上同其他哲學家有共同之處,所以後世學者在研究他們的學說時,無論僅僅從信仰維度或神學視角出發,還是僅僅從理性維度或哲學視角入手,都難免有失片面。然而自近代以來,隨著哲學與神學的漸行漸遠,這種調和主義的思維方式開始遭到教內外的部分學者的抨擊,甚至有少數學者對於士林哲學作為一種基督宗教哲學的性質也表示反對,從而引發了當代哲學史界關於基督宗教哲學概念本身的合理性之爭。
壹、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合理性之爭的由來
嚴格說來,“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合理性”之爭發端於20世紀的某些西方哲學史家,但早在哲學尚被看作“神學之婢女”的中世紀,已有人對哲學真理與神學真理的統一性產生懷疑。如13世紀拉丁阿威羅伊主義者西格爾(Sigerus de Brabant)曾稱“我們從啟示中獲得的那些關於靈魂的真理並不能被自然理性所證實。”14世紀新唯名論者奧卡姆(William Ockham)更是按照“如無必要,切勿增加實體”的標準,否定了哲學家通過理性來論證部分神學教條的可能。因此有學者評價:“奧卡姆及其學派皆在中世紀後期起著分離理性與信仰以及削弱教權的作用,這實際上是促進經院神哲學解體的過程。”
傳統的士林哲學解體後,其調和信仰與理性的思維方式遭到比以往更激烈的批評。如黑格爾(G. W. F. Hegel)批評它說:“對於這種神學,基督教的絕對世界乃是一個被當作現實性的體系,正如智者派把普通的現實性當作真正的現實性一樣。於是便主要地只剩下思維的規律和抽象概念屬於真正的哲學範圍了。至於這個基督教的世界如何被認作基礎,則常常發展到極為可笑的程度。”羅素(Bertrand Russell)更宣稱:“阿奎那沒有什麼真正的哲學精神。他不像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那樣,始終不懈地追逐著議論。他並不是在探究那些事先不能預知結論的問題。他在還沒有開始哲學思索前,早已知道這個真理;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公佈的真理。”受其影響,一些學者甚至公開否定了士林哲學作為一種基督宗教哲學的性質。如布裏葉(Emile Bréhier)稱,以多瑪斯主義為代表的士林哲學在信仰與理性的雙重約束下陷入矛盾,從而分裂成“非基督宗教的哲學和非哲學的基督宗教。”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也認為,因神學強調信仰和教義的權威,而哲學依靠理性和問題意識,故基督宗教哲學的概念就如同“木的鐵”或“圓的方”等概念一般荒謬。
為回應上述批評,當代一些新士林哲學家或新多瑪斯主義者曾試圖通過論證基督宗教信仰同士林哲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及其對後者的積極作用,來為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合理性辯護。如吉爾松(Etienne Gilson)聲稱:“如果定義這一哲學的標準不是它借鑒的內容,而是它的原創性和它的內在精神動力,那麼我們在其中找到的就既非亞裏士多德主義,亦非柏拉圖主義,而首先是基督宗教。”他還和馬裏旦(J. Maritain)等人一起,在1931年法國哲學協會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同否定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布裏葉和布倫施維格(Léon Brunschvicg)等人展開了正面辯論。馬裏旦宣稱,士林哲學不可能獨立於“基督教的狀態”之外,而“這種狀態對於哲學藉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具有決定性影響。”此後,又有更多學者加入這場辯護。如克裏茲曼(N. Kretzmann)和斯湯普(E. Stump)認為,“多瑪斯主義的上帝已如此徹底的理性化,以至他把那些教義訴諸理論的時候,總被這樣一種預期所引導,即哲學與神學應是相互印證而非相互抵觸的。”麥金裏(R. McInerny)在評價多瑪斯主義的哲學價值時指出:“其哲學的獨創性與心靈的豐富是在建構神學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在其哲學與神學相交匯的地方,我們總能看到這種交匯產生的亮光”。摩爾(Armand A. Maurer)和戴維斯(Brain Davies)等亦提出,多瑪斯主義已將“哲學之水”釀成“神學之酒”,因而“不可能從中抽出一個可以被視為純哲學的部分。”
然而,並非所有的新士林哲學家都認同基督宗教哲學的概念。如耶穌會學者柯布登(Frederick Copleston)認為,多瑪斯主義的哲學是一種建立在“理性自主”原則上的哲學,其結論之所以同基督宗教信仰一致,並非因為信仰的干預,而是理性與信仰的不謀而合,所以“僅就這種哲學與基督宗教是相容的這點而言,不少多瑪斯主義者才同意稱其‘基督宗教哲學’。但事實上,如果因為一種哲學可以與基督宗教相容便稱其基督宗教哲學,那麼同那種因為某種數學可以與基督宗教相容就稱其基督宗教數學的說法相比,它似乎並不更有說服力。” 新士林哲學魯汶學派的斯汀伯格(Von Steenberghen)也表示:“神學代表一條朝向上帝的上升之路,哲學則代表一條背向上帝的下降之路。正如一條道路不可能既是下降的又是上升的,一種哲學也不可能既是理性的又是基督宗教的。” 這些教內人士之所以也不願把士林哲學定義為基督宗教哲學,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把其中的哲學內容從神學的上下文中分離出來,以通過吸收現代哲學和科學理論的辦法加以創造性發展。
20世紀中期以來,新士林哲學的影響有所減弱,但關於士林哲學是不是基督宗教哲學的爭論並未停止,而是吸引了更多學者的參與。如萊登賽爾(Maurice Nédoncelle)分析說,士林哲學“反映了一條看待信仰與理性之關係的新思路。實際上,人的理性要求得到獨立。對聖安瑟爾謨來說,它是一項在原始的超自然主義背景中提出的要求;對阿奎那來說,它本身就有一個與啟示平行的系統,這系統雖低於啟示,但在其根源和原則上卻是獨立的…《反異教徒大全》甚至採用異教徒本身的觀點來論證他們反對的基督宗教教義。這是一種哲學式辯護,而非神學式辯護。” 相反,肯尼(Anthony Kenny)則指出,儘管多瑪斯主義同基督宗教信仰有“歷史聯繫”,但“這種歷史聯繫並不意味著不能把他的哲學與神學分割開來進行研究,也不意味著神學目的主宰了哲學,從而使它成為一種不自由的或非哲學的東西。在神學著作中有大段‘純哲學’部分,其哲學性質如此之純,以至神學家有時必須對它們的意思加以嚴格限制,才不會導致神學困難。” 麥金裏(Ralph McInerny)也指出,儘管多瑪斯主義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間有密切聯繫,但其基本方法是哲學的而非神學的。
貳、爭論雙方的分歧焦點及主要理由評析
在某些否認士林哲學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基督宗教哲學的學者看來,這種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間的聯繫只是偶然的和外在的,而非必然的和內在的。然而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學者從贊同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立場,對他們的上述觀點及其提出的各種理由加以針鋒相對的反駁。總的來看,雙方的爭論是圍繞以下三個主要環節展開的。
首先,一些反對把士林哲學定義為基督宗教哲學的學者聲稱,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某個數學家或生物學家是基督徒,便把他的學說稱為“基督宗教數學”或“基督宗教生物學”,也不能因為某個哲學家是基督徒,便把他的學說稱為“基督宗教哲學”。 針對上述說法,吉爾松等反駁說,即便一個人在研究數學和生物學時,真的可以不受自身宗教信仰影響,他在研究某些為哲學和神學共同關注的問題時,卻不可能完全做到這點,因為“在我們和希臘人之間已介入基督宗教的啟示,而這一事實已深刻改變理性工作的基本條件。如果你有啟示,那麼你在研究哲學時如何能變得好像未曾聽過它一般?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錯誤正是純粹理性的錯誤,而任何試圖自鳴得意的哲學將再次陷入這種錯誤或其他更嚴重的錯誤;故而從今以後,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以啟示為嚮導,並努力理解啟示的內容——對啟示的這種探討就是哲學本身。” 就此而論,不僅中世紀士林哲學是名副其實的基督宗教哲學,甚至某些以理性主義為標榜的近現代哲學也是有實無名的基督宗教哲學。如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指出,在談到西方哲學的傳統時,不能僅考慮希臘羅馬哲學,而應包括《聖經》,因為啟蒙運動後的很多哲學家依然在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後者的影響。
第二,把基督宗教哲學視為一個“矛盾概念”的布裏葉等聲稱,某些士林哲學家之所以能得出符合信仰的結論,並非是出自必然的邏輯推理,而是受到了當時教會推崇的權威教義的外在限制。例如,多瑪斯主義對基督宗教信仰與亞裏士多德哲學的調和非但未能在兩者間建立內在的聯繫,反而使自身受到兩個相衝突的原則的約束,即一方面堅持“哲學是神學的婢女”的信仰主義原則,另一方面又難以拒絕“理性自主”的亞裏士多德主義原則。 針對上述觀點,吉爾松和馬裏旦等提出反駁說,信仰對於士林哲學並非只是外在的指導性原則,而是一種具有超自然性的“建構性要素”(constitutive nature),因為“在任何一種名副其實的基督宗教哲學中,都有啟示作為理性的必要補充,儘管它在形式上保持著兩者(啟示與理性)的區別。按這種理解,基督宗教哲學的概念所表明的並非一個可以抽象定義的單一本質,而是某種需要描述的歷史事實。”
第三,在某些反對把士林哲學稱為基督宗教哲學的學者看來,哲學的前提必須是普遍的自明真理或有可靠的經驗證據,而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啟示顯然不符合這一標準。正是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柯布登等一部分新士林哲學家才辯解說,以多瑪斯主義為代表的士林哲學同樣是建立在普遍的理性前提之上和處在自然理性的引導之下,而且儘管其中混雜著大量的神學內容,但從中“抽”出“一種完全與神學無關的純哲學”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在很多學者看來,以這種方式來為士林哲學作辯護是毫無必要的。如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指出,即便一種哲學的前提並非“不證自明的真理”,也不意味著它對這些前提的論證必然陷入康德所說的“二律背反”,況且康德的“二律背反”本身也不是公認的真理。 阿爾斯頓(William Alston)進一步指出,基督宗教信仰並不缺少經驗基礎,只是在某些信奉“經驗主義教條”者看來,它們依據的是不可靠的宗教經驗。但正如當代科學中的“不確定性原理”揭示的那樣,通過任何途徑得來的經驗證據都不是絕對可靠的。 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還指出,哲學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普遍公認的理性前提,而且在心靈哲學、科學哲學、政治哲學等哲學分支中,哲學家們更是常常因不同的前提發生爭論,所以不能因為基督宗教哲學採用了其他人不接受的前提,就否認其哲學意義。
參、基督宗教信仰在士林哲學中的作用之辯
近代以來,隨著理性主義和所謂的“科學主義”的盛行,信仰在哲學中的作用常常被一概貶為消極負面的因素。如黑格爾宣稱,士林哲學家因為對神學和哲學的混淆而束縛了理性的自由和發展,其理論實質是“為了靈明世界的利益而在抽象概念中繞圈子。” 羅素亦指出,以多瑪斯為代表的士林哲學家缺少真正的哲學家所具備的那種理性精神,所以只配稱為亞裏士多德的“拙劣模仿者”。 面對上述指責,部分教內學者也曾試圖通過切斷信仰同理性的聯繫,來為信仰尋找出路。他們要麼像施萊爾馬赫(Fredrich Schleiermacher)那樣把信仰定義為一種非知識亦非道德的情感,以擺脫為信仰提供理性辯護的責任, 要麼像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那樣把神學和哲學視為兩個相互隔絕的領域,以說明信仰有權拒絕理性的批評。 即使在當代的新士林哲學家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試圖通過放棄基督宗教哲學家的身份,來消解信仰與理性之間的張力。
然而,儘管任何宗教信仰中都包含某些非理性因素,但如果僅把信仰定義為非理性的情感或意志,則無異於把它視為動物式的本能或愚蠢的盲從。因此,也有很多新士林哲學家不同意分割信仰和理性的做法,而認為信仰非但不是“理性的敵人”,反而是理性的補充或基礎。如吉爾松指出,“對於那些名副其實的基督宗教哲學家來說,信仰能對他們的思想起到一種簡化作用,而在那些可以直接受到信仰的影響的領域,即在探討上帝、人類及其相互關係的教義時,他們的原創性得到特別出色的發揮。” 馬裏旦也指出:“哲學一方面服務於神學,另一方面也從後者獲得有價值的幫助以為報償。第一,正因為它在性質上要隸屬於神學的外表控制和消極管束,所以它就受到保衛,不致犯許多錯誤;如果它犯錯誤的自由這樣的有著限制,它的達到真理的自由便因之而獲得保障。第二,正因為它是神學的工具,所以它才被導誘著以更大的準確性和更微妙的精密性,去替某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論下定義;但如果它被放任自由發展,就會陷於把這些概念與理論忽略掉的危險。”
這些新士林哲學家還試圖以基督宗教信仰在中世紀士林哲學中的積極作用為例,來說明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合理性。如吉爾松稱,信仰和啟示不僅可以幫助人們認識上帝,還有助於人們認識自身,因為“假如我們想徹底認識人,就必須徹底研究身體和靈魂。正如我指出的,中世紀士林哲學家絕未忽視身體研究,但他們的身體研究與其說屬於哲學史,不如說屬於科學史。他們之所以竭力關注靈魂,是因為靈魂有上帝的形象,而正是在這一領域,來自基督宗教的影響理所當然地結出了最豐碩果實。” 馬裏旦也稱,由於士林哲學家可以得到信仰的幫助,所以比那些僅僅依靠理性的哲學家更有優勢,如多瑪斯之所以能克服亞裏士多德的諸多局限,正因為“當他憑籍著他的作為神學家的天才將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利用為神聖科學(這可以說是‘天主自己的知識之加在我們心靈上的一種印痕’)的工具時,可以把那個哲學放到一種更高超的光的照明下去,從而把它提高到它本身以上,因為這種光可以使它本身獲得一種與其說是人性的,卻無寧說是神性的光彩。”
除了這些新士林哲學家,還有不少學者試圖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論證信仰對哲學和理性的積極意義。如普蘭丁格指出:“基督教的信念是恰當的基礎信念,這恰當性包括了三項我們所討論的知識價值。在這模型裏,信徒接受這些信念為基礎信念,是擁有辯護的,也是合乎理性的(內在的和外在的),而且,這些被接納為基礎的信念是可以有保證的,足夠的保證使之成為知識。” 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則從利用“簡單法則”解釋世界的必要性出發,來說明基督宗教的一神論信仰同樣能對世界做出合理的簡單解釋,因而是可以作為科學基礎的“超科學解釋理論”(super-scientific explanatory)。 還有學者試圖通過對信仰或理性的重新定義,來徹底化解兩者的衝突。如孔漢思(Hans Kung)稱,信仰的本質不是“非理性”,而是對解決某些終極問題的“基本信賴態度”,因而在信仰與理性之間“既不應該搞敵意的衝突,也不應該主張自由放任的共存。應當做的是在一起進行批判性對話,尤其是在神學和哲學、神學與科學以及人文學、神學與文學之間進行對話;宗教與理性是一致的。” 田立克(P. Tillich)稱:“理性是信仰的條件,信仰是理性的實現。作為一種終極關切狀態的信仰就是理性。信仰與理性在本質上並無衝突,而是彼此包容的。” 潘能伯格亦指出,信仰(尤其是末世論信仰)對理性的積極作用體現在“理性的歷史性”,因為任何理性認識只有面向“未來的終結”時,才能獲得其真正的意義。
雖然他們的上述辯護並未得到當代學術界的普遍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西方學者長期以來對士林哲學的某些偏見。在20世紀中期前,大多數西方哲學家尤其是分析哲學家均把基督宗教信仰對士林哲學的影響一概視為消極負面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哲學的首要任務是澄清語言的意義,以把一切無法通過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命題從哲學中驅趕出去。但近幾十年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對士林哲學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如英國的肯尼和美國的克裏茲曼(Norman Kretzmann)等分析哲學家雖然沒有直接把士林哲學定義為基督宗教哲學,但他們已不再把基督宗教信仰對士林哲學的影響完全看成消極負面的。在肯尼看來,“沒理由因為一個哲學家為他已經相信的東西尋找理由而對其橫加指責…羅素就曾以此為由來否認阿奎那是真正的哲學家。但令人驚訝的是,羅素本人的《數學原理》竟然花了一百多頁篇幅論證1加1得2。這可是一個他終生堅信不疑的東西。” 他還進一步指出,由於士林哲學家在論證信仰的過程中提出了某些具有“不朽性和永恆性”的問題,所以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論述“沒有像中世紀的邏輯學和自然哲學那樣,被文藝復興以來科學的巨大進步所淘汰,而仍然包含著許多有價值的、創造性的思想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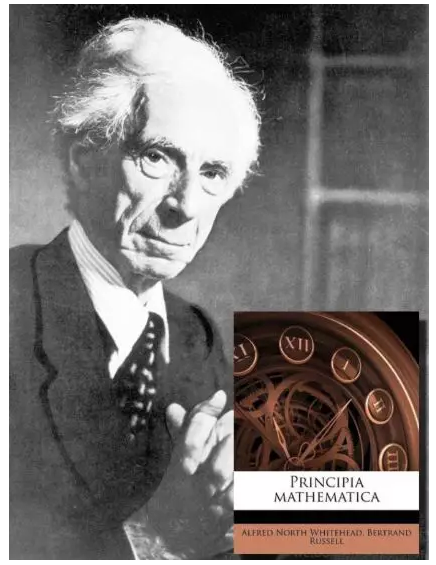
肆、結語
關於中世紀士林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間究竟有無內在聯繫這個問題,當代學者的爭論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信仰在哲學中的作用的不同認識。一方面,吉爾松、馬裏旦以及後來的普蘭丁格、因瓦根和阿爾斯頓等人之所以堅持認為士林哲學同基督宗教信仰之間有真正的內在聯繫,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信仰對哲學的影響不僅是內在的,而且是積極的。用吉爾松的話說:“除非(基督宗教哲學)這個詞完全沒有積極意義,我們才必須坦承,惟有啟示與理性的內在聯繫才能足以賦予它以意義。” 另一方面,部分學者之所以不願承認基督宗教信仰同士林哲學之間有真正的內在聯繫,則因為他們要麼把信仰僅僅視為一種對理性的外在干擾或束縛(如布裏葉、海德格爾等),要麼企圖證明聖多瑪斯·阿奎那等人的哲學並未受到信仰的外在限制,而只是在自然理性的引導下得出了與信仰一致的結論(如柯布登、斯汀伯格等)。可以說,儘管這部分學者拒絕接受基督宗教哲學概念的動機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把信仰對哲學的影響看成了消極負面的並因而需要排除的因素。然而,通過對基督宗教信仰同士林哲學之間的聯繫及其對後者的作用的具體分析,我們發現這種聯繫和作用並非是完全一致的和固定不變的。在士林哲學史上的不同時期、不同學派、不同人物及其對不同問題的探討中,這種聯繫和作用往往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不否認,某些士林哲學家可能因為顧及信仰的權威而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例如,正像萊登賽爾所看到的:“在拉丁教會的心臟地帶,也可以發現像布拉邦特的西格爾一樣的阿威羅依崇拜者,此人在哲學引導下得出了違背啟示的結論,並由此陷入一種痛苦境地,因為他本人仍想堅持基督宗教的真理。甚至聖文都辣也無法完全拒絕亞裏士多德。” 僅就此而論,我們不排除在士林哲學中,信仰有時可能成為一種對理性的外在限制並由此產生某些消極影響。但我們更應看到,還有很多士林哲學家曾從論證和解釋信仰的特殊需要出發,對前人的哲學觀點做出創造性發展,並由此在某些方面取得超越前人之上的哲學成就。如聖多瑪斯為防止有人把亞裏士多德的“主動理智”解釋為全人類共有的理智,從而同個人靈魂不朽的教義相衝突,而創造性地提出了每個人的“主動理智”都各不相同的新觀點,並用“習性”(habitus)的概念更好地解釋了思維活動的非連續性。 可見,至少對於一部分士林哲學家來說,信仰曾為他們提供發現問題的契機和重新審視前人哲學觀點的視角,因為正如某些當代學者所認識到的,“當基督宗教信仰介入到一種傳統中時,它提供了一種重新審視該傳統的角度,使得傳統在基督宗教信仰中展示出新的泉源。就基督宗教與希臘傳統而言,希臘主義固然可以從希臘的思辨和哲學的構成及其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來理解何謂希臘,但基督宗教信仰也提供希臘主義以重新審視邏各斯、上帝、知識和信仰的角度,使希臘傳統在其衰落的景況中有根本的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信仰對理性的促進作用不僅可以存在於士林哲學這種典型的基督宗教哲學中,而且存在於某些有實無名的基督宗教哲學中。如近代理性主義哲學的奠基者笛卡爾雖未直接訴諸信仰和啟示的權威,但他不僅宣稱“真正的哲學”不可能同“真正的宗教”相衝突,而且把證明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當作其“第一哲學”的首要任務。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雖反對把上帝當作解決哲學難題的“救急神”,但他的“前定和諧說”同樣源自基督宗教信仰的啟發。同時,即便在少數把哲學貶為“異教徒的智慧”的神學家那裏,信仰與理性也並非始終處於敵對狀態。如早期護教士特土良(Tertullian)雖宣稱“基督徒與你們的哲學家在認識和方法上,都沒有什麼相似之處,” 但又承認“我們有時候必須從我們的對手那裏借用這一類清晰明白的證據。” 反多瑪斯主義的新教領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雖依照“因信稱義”的原則把一切脫離信仰的理性斥為“魔鬼的新娘”,但又把合乎信仰的理性稱為上帝“最重要的禮物”和“神學最有用的僕役”。
總之,在探討基督宗教信仰同士林哲學之間的關係時,我們應避免某些西方學者表現出的絕對主義態度,而應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方法來加以區別對待。用這種方法看問題,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中世紀士林哲學家並非都將哲學完全建立在“理性自主”的原則之上,而往往在前提和方法上受到信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很多情況下,信仰非但沒有扼殺他們的理性思維,反而為他們提供了發現問題的契機和異於前人的視角。因此,儘管他們的學說是以論證和解釋信仰為首要目的和基本方法的,但是只要他們能按照理性思維的基本規則對信仰做出合乎邏輯的論證解釋,我們便不能因為他們使用了某些不同於其他哲學的前提和方法,就一概否認他們的學說是一種真正的基督宗教哲學。

作者:徐弢
原文发表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2018年4月刊